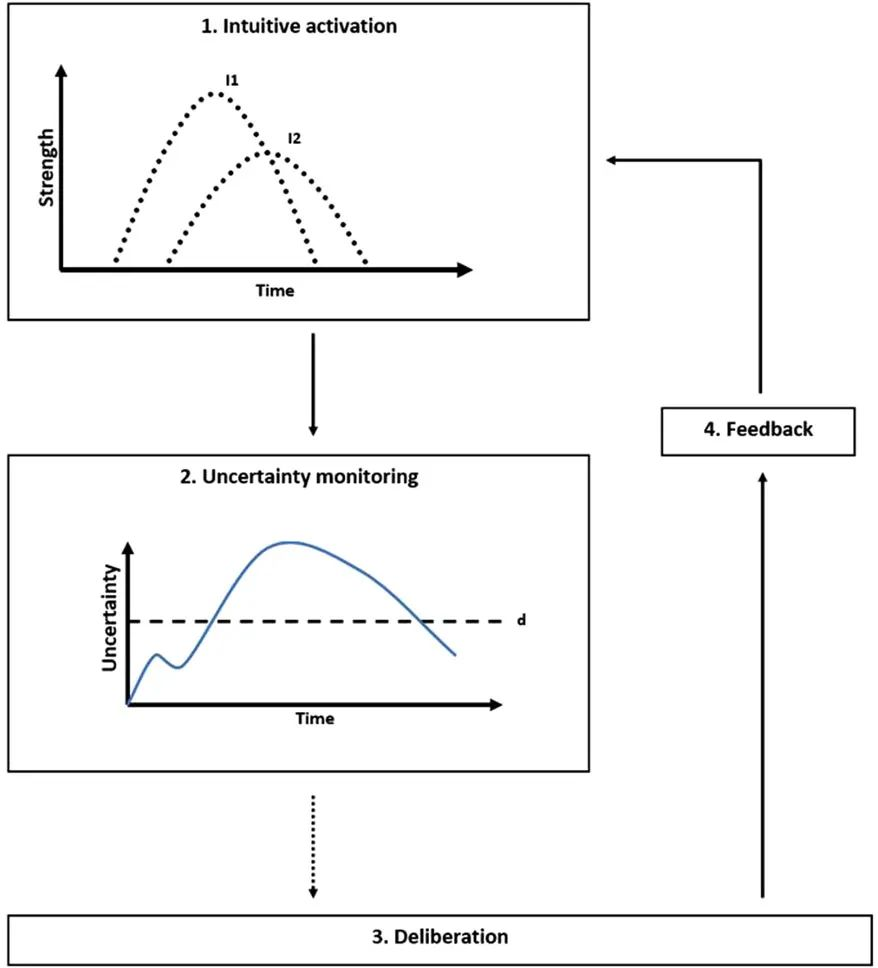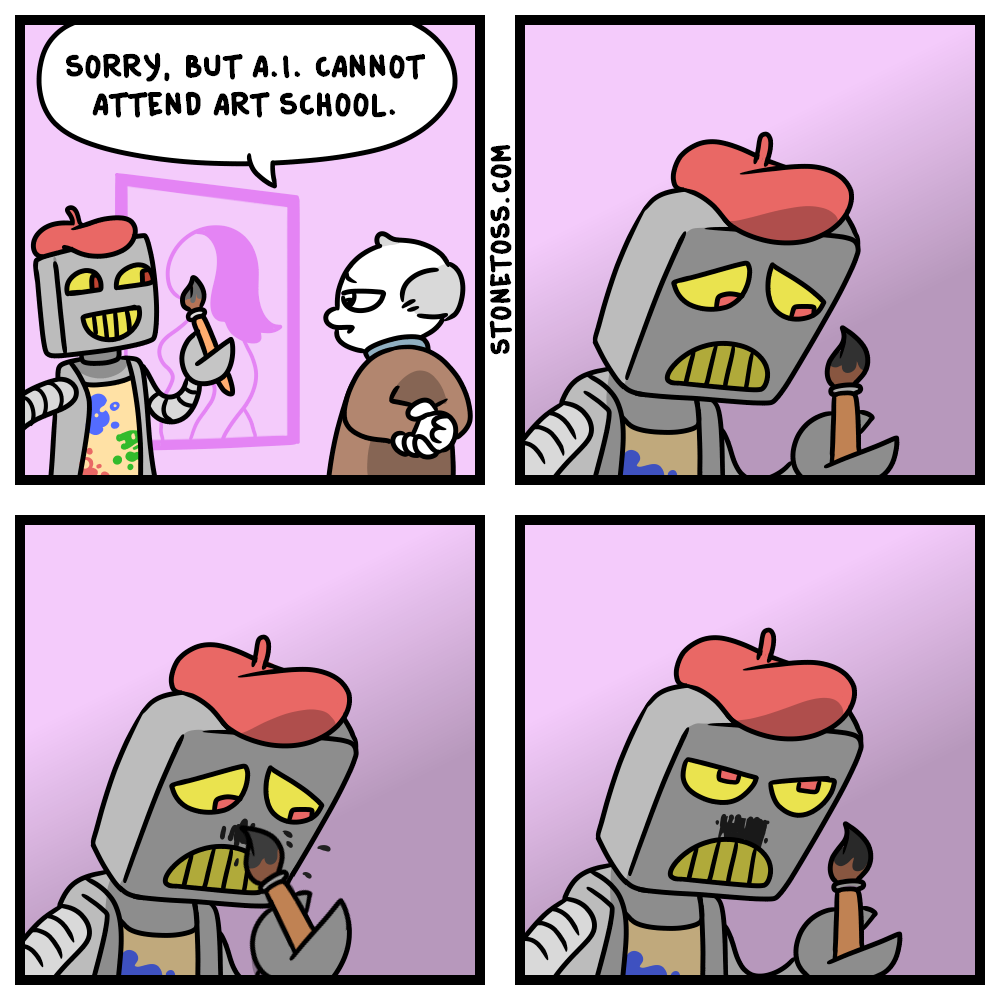人是善变的,可以前一秒兴致高昂,下一秒绝望万分。我们可以在前一个小时,为绝望的人生做满三十年的计划,但是在做完的一瞬间,发现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而一个解脱的窗户就出现在面前。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5501570/
1、婴幼儿的突触修剪
《发展心理学》罗伯特·S.费尔德曼
3.1 婴幼儿期的生理发展
婴幼儿出生时一般有1 000亿~2 000亿个神经元。事实上,在出生前的某些发展阶段,细胞分裂已经使得神经元以每分钟250 000个的速度增加。刚出生时,婴儿大脑中的绝大多数神经元和其他神经元之间的联结相对较少。但在出生后的前两年,婴幼儿大脑中的神经元将会建立起数十亿的新联结。事实上,神经网络会随着个体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而且神经元联结的复杂性在人一生中都会不断增长。在成年期每个单独的神经元都可能和至少5 000个神经元或身体的其他部分相连。
突触修剪
尽管随着经历的改变,人一生中突触都在不断地形成,但婴儿出生时所具有的神经元数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所需要的,而其在前两年中形成的数十亿个新突触更是远远超过了所需。大脑的发展是通过去掉多余的神经元来增强特定能力的。随着婴幼儿经验的增加,那些与其他神经元没有联系的神经元就显得多余了,它们最终会消失,从而提高神经系统的效率。随着多余神经元的减少,剩余神经元之间的联结会因为婴幼儿在生活中是否使用它们而得到相应扩展或消除。生活中没有受到刺激的某些神经联结,就像没有使用的神经元一样会被消除,让已有的神经元和其他神经元建立更加完善的交流网络,这个过程叫突触修剪(synaptic pruning)。神经系统的发展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方面的发展,它会通过损失部分细胞来提高发展效率。
随着神经元的生长,它们会改变位置,并按照功能进行重组。一些神经元到了大脑的表层,即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另外一些神经元则到达大脑皮层下的亚皮质层。在出生时,大脑皮质下这部分是发育最完善的,它负责调节呼吸、心率等基本活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皮层中负责思维与推理等高级活动的细胞会变得更加发达,并彼此产生更多的联系。
环境对大脑发展的影响
由于遗传预先决定的模式,大脑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发展的,然而大脑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大脑的可塑性(plasticity)相对来说非常强,可塑性就是发展中的结构和行为可受经验改变的程度。脑损伤的儿童通常会比有类似情况的成人所受的影响小,也更容易痊愈,这就是高度可塑性的体现。在婴幼儿能力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特定并且有限的敏感时期,儿童对环境的影响或刺激特别敏感。一个观点认为,除非在敏感期让婴幼儿接受一定水平的环境刺激,否则婴幼儿的能力就会受损或无法发展出来,并且此后永远也无法完全弥补这些能力。
2、伦敦出租车司机
《大脑的故事》大卫•伊格曼
1 我是谁
成人的大脑定型了吗
科学家们发现伦敦出租车司机们的大脑有着明显的改变:他们的海马后部明显变得比对照组的大了许多,这大概是不断增加的空间记忆造成的。研究人员还发现,出租车司机做这份工作越久,大脑该区域的变化就越大,该结果表明这些司机不是在进入这一行时海马区域就大于常人,这是实践所带来的变化。对出租车司机的研究表明,成年人的大脑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进行重新配置的,且变化程度之大是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能看得出来的。
3、环境塑造论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
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SPE):体制力量(环境)创造强大的社会情境,并在情境中影响所有人的行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曾是和平主义者和“好人”的学生在扮演狱警时表现得具有攻击性,甚至做出残暴的虐待行为。心理稳定的学生扮演囚犯时很快就表现出病态行为,产生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olessness),屈服于这种命运。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蝇王》(Lord of the Flies)
4、逆境能永久改变我们的大脑
人的经历会塑造他们的大脑,逆境会导致大脑功能的持久改变。
《A stable and replicable neural signature of lifespan adversity in the adult brain》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3-023-01410-8
https://www.msn.cn/zh-cn/news/other/科学家发现逆境能永久改变我们的大脑/ar-AA1fEfZ3
5、你眼中的世界和别人的一样吗?
https://mp.weixin.qq.com/s/Rgbcj04BZaZVm_iF73LcKg
人老了,看到的颜色都和年轻人不一样?
伦敦大学学院的最新研究发现,健康老年人与年轻人在颜色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研究人员测量了在黑暗环境中受试者对各种颜色反应时的瞳孔响应,共涉及17名年轻成年人(平均年龄27.7岁)和20名老年成年人(平均年龄64.4岁)。研究人员使用眼动追踪(每秒记录1000次瞳孔直径),在受试者眼前展示了26种不同的颜色,每种颜色都有特有的亮度和饱和度。结果显示,老年人的瞳孔对颜色饱和度的收缩反应减弱。然而,对于颜色的亮度,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反应相似。研究还补充了之前的行为研究成果,即老年人感知到的表面颜色不如年轻人丰富多彩。
Pupil responses to colorfulness are selectively reduced in healthy older adults. Scientific Reports, 13(1), Article 1.
van Leeuwen, J. E. P., McDougall, A., Mylonas, D., Suárez-González, A., Crutch, S. J., & Warren, J. D. (2023).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3-485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