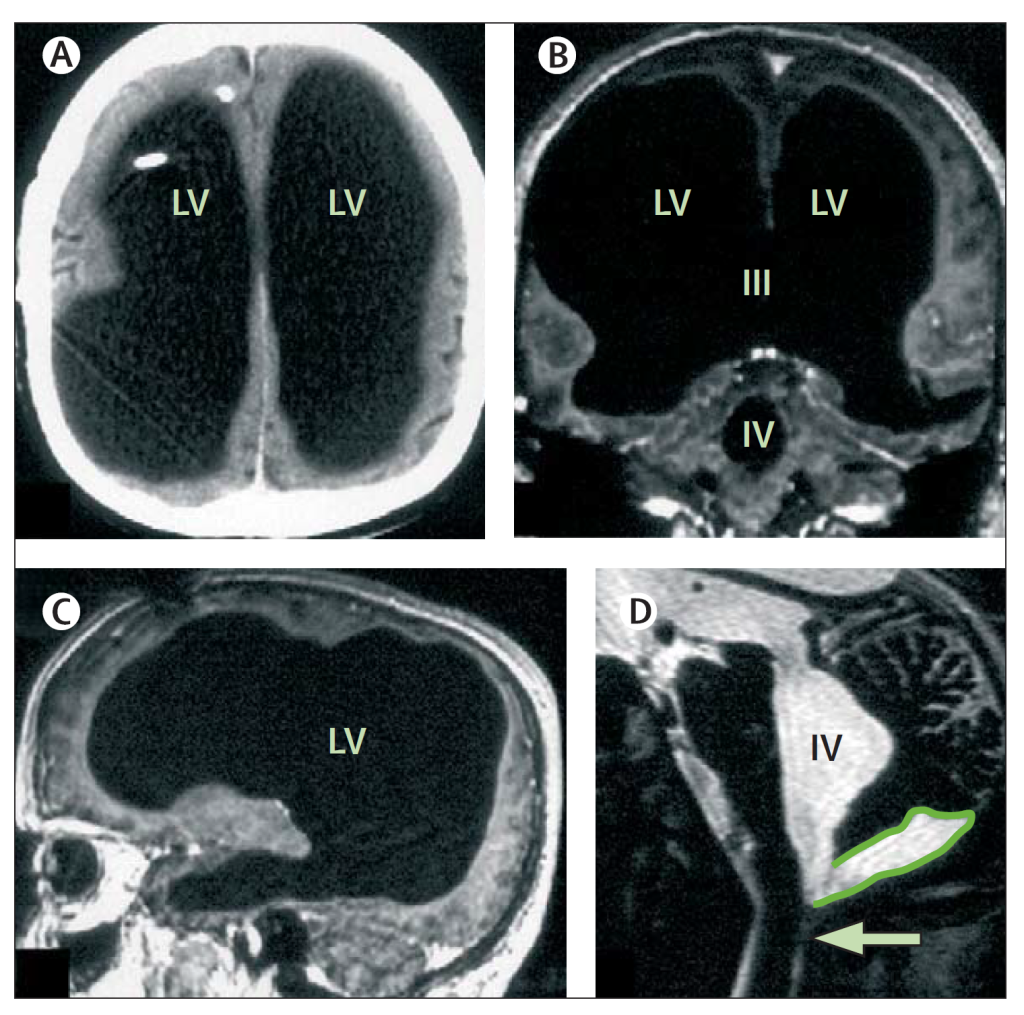第一步:有机物的原始汤中涌现出大量不同类型的有机自复制体,但这些有机自复制体的复杂性是代际衰减的;
《AI众神时代》乔治·戴森
15 数字生命,机器的自我繁殖 自复制自动机
自动机能制造出不逊色于自身复杂度的后代吗?冯·诺伊曼:“较低水平的‘复杂性’可能随着代际退化,也就是说,每个能够制造其他自动机的自动机,只能产生复杂性不如自身的自动机。然而,存在一种特定程度的复杂性,如果安排得当,可能会使自动机合成现象产生震天撼地的结果。换句话说,每一个自动机合成生产的自动机,可比自身更为复杂,具有更高的潜力。”
第二步:自复制体进化出通过类似RNA、DNA数字形式的遗传信息传递能力,用数字化来保证代际复杂性的维持;
12 操纵进化,巴里切利的基因宇宙 生物进化与数值研究
“我认为,一个真正经济、有效的生物体是‘数字’和‘类比’原则的结合。”冯·诺伊曼在1951年发表的《不可靠元件构成的可靠结构》的初稿中这样写道,“‘类比’程序使进化过程丧失精确性,从而相当快地危及进化的意义……因此‘类比’方法可能不能单独使用,应不时介入‘数字’方法以实现重新标准化。”他强调,复杂生物要在嘈杂、不可预测的环境中生存,就必须使用数字纠错代码定期复制自己的新副本—此番言论出现之后不久,就发现了活生物体的繁殖是如何通过复制编码为DNA的指令串来协同进行的。
数字生物—无论是核苷酸串还是二进制代码串,可能会发现定期将自己翻译成模拟的、非数字的形式是有利的,这样,对于歧义的容忍性、对非致命错误的引入以及收集有形资源的能力可以帮助它在纯数字领域中存活。冯·诺伊曼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第四场讲座中解释说,如果“每一个错误都必须捕捉、解释和纠正的话,那么一个复杂的生物体都活不过一毫秒。这种理念完全不同于那种宣称只要有错误就会导致世界末日的理念”。
第三步:通过:
1、基因突变的随机性 + 环境筛选:传递环境的模拟信息;
2、转座子、表观遗传、形态发生、有性繁殖等:传递环境的模拟信息;
1.1.2.4.1 基因层面的创新 http://47.92.147.95/index.php/2024/10/13/1130/14/
3、生长发育过程、意识过程(身体各个系统/器官的生长发育过程、大脑全局工作模式的统计性过程):传递环境的模拟信息;
获得模拟计算(连续计算)能力,突破DNA数字形式系统所固有的逻辑局限性,实现代际复杂性的增长。
关于形式系统所固有的逻辑局限性:
形式系统无法完全捕获数学真理,机械计算无法解决所有数学问题。任何足够复杂的形式化推理系统都内在地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我们无法得到一个既能包罗所有数学真理,又能在有限步骤内证明所有真理,且能证明自身一致的系统。
-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 (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s):任何足够强的一致(无矛盾)形式系统都存在一个在该系统中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命题;
- 停机问题 (Halting Problem) :机械计算存在原则上无法通过算法解决的判断问题;
- 邱奇-图灵论题:任何可计算函数都能被图灵机计算,图灵机刻画了“可计算”的极限,而停机问题等表明存在不可计算的函数/问题;
- 多世界与相对一致性(选择公理与连续统假设的独立性):不同系统可能在不同框架下一致,但无法在自身中证明。
人类直觉可以超越任何固定的形式系统,因为我们可以不断承认新的公理来证明之前不可判定的命题(尽管这又会形成一个新的更强系统,同样受不完备性约束)。
13 制造会思考的机器,人工智能初探 机器已经“长大”
人工智能的悖论在于,任何简单到可以理解的系统会因为不够复杂而无法达到智能水平,而任何复杂到可以达到智能水平的系统也不会简单到可以被理解的程度。
14 社交网络,一台庞大的模拟计算机 模拟向我们走来
正如杰克·古德在1962年所说,部分问题在于“模拟计算机这个名字起得很愚蠢,它们应该叫作连续计算机”。对于现实世界的问题,尤其是模棱两可的问题,模拟计算不仅在计算答案方面,而且在提出问题和传达结果方面,表现得更加快速、准确和稳健。